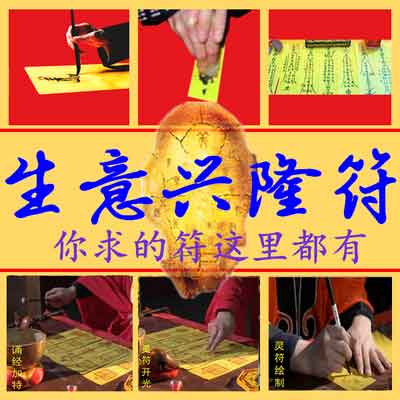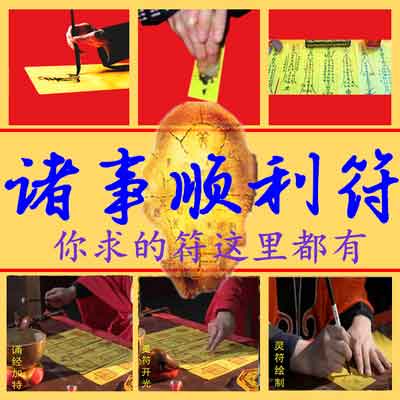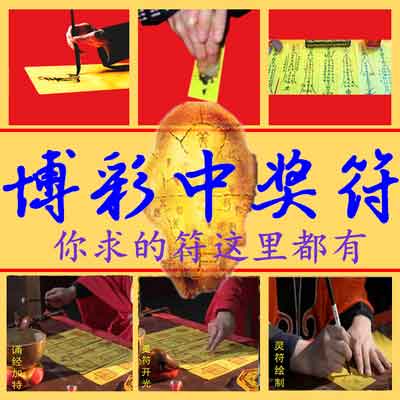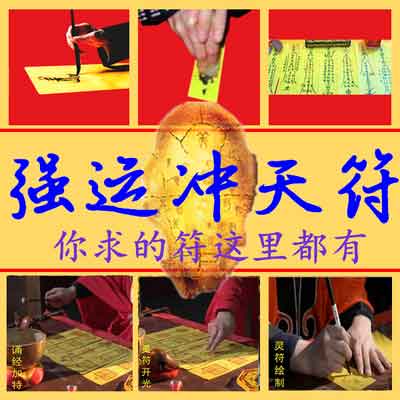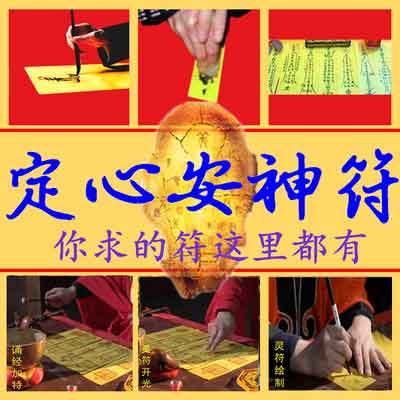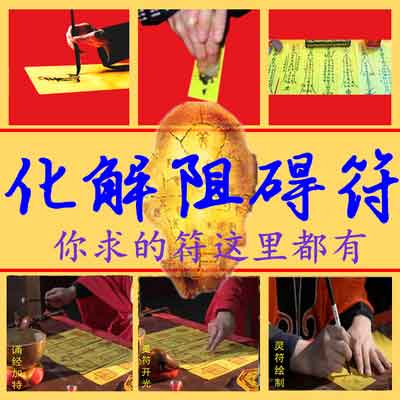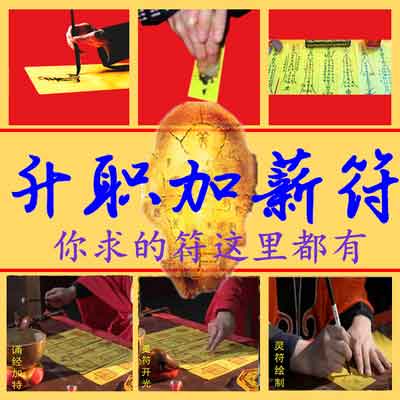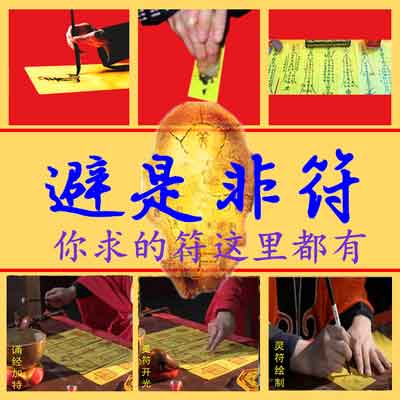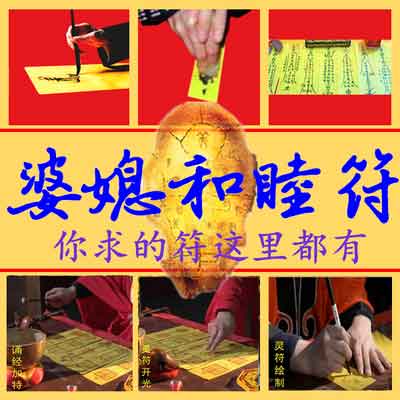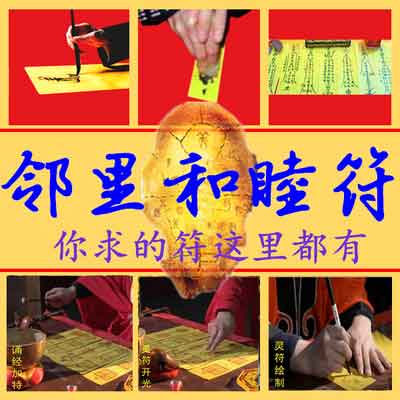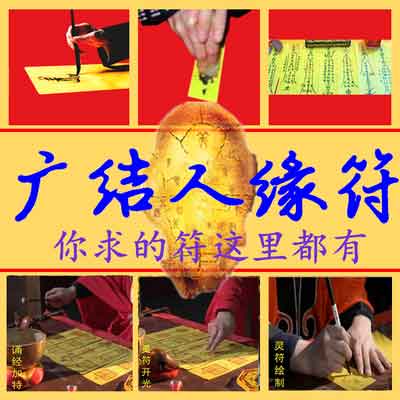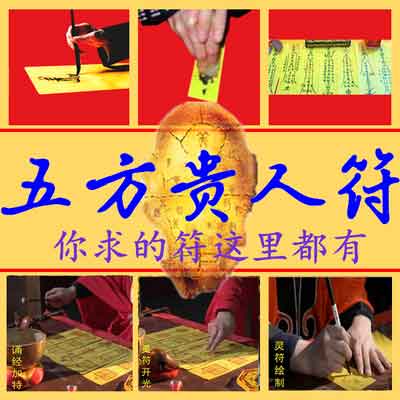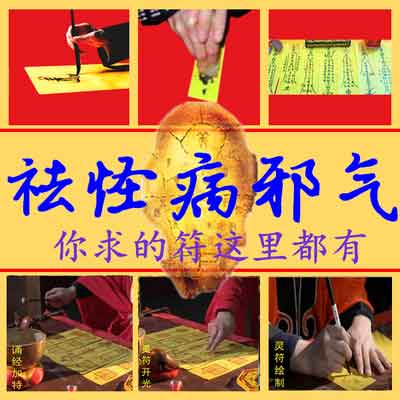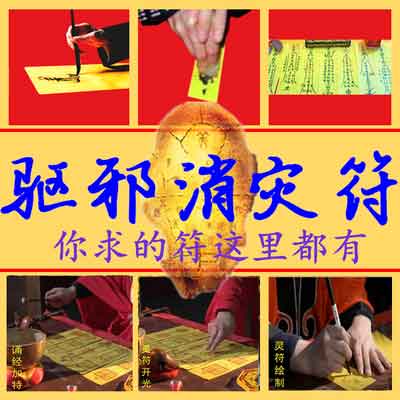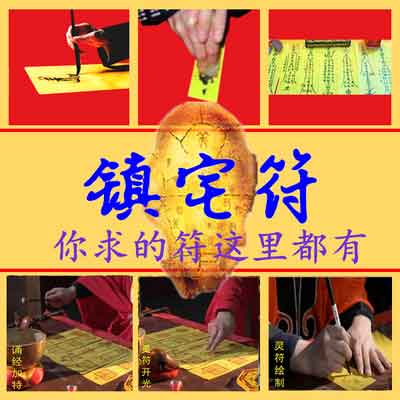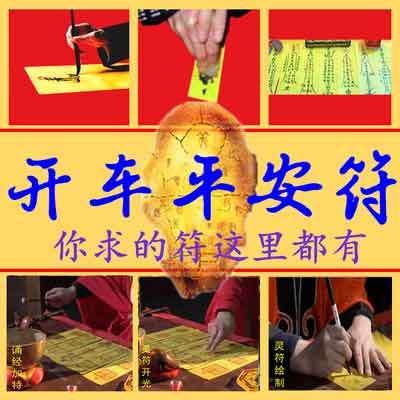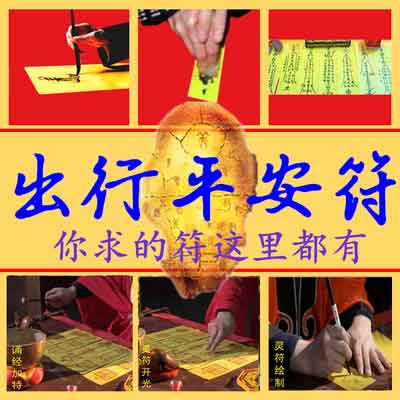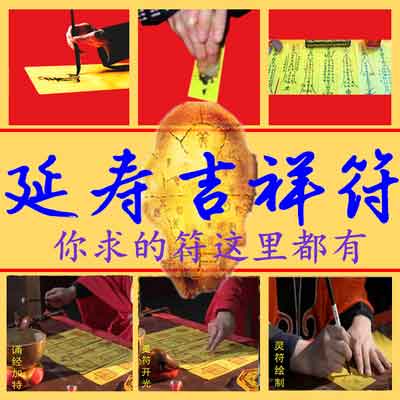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8)巫蛊故事的基本定型
宋代对于“巫蛊”的想象更加细腻、翔实,并出现了新的想象内容。被后世诸多小说认为是各种蛊虫中毒性最强的金蚕蛊就在这一时期出现。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这样论述:
“金蚕始於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食中以毒人,人即死也,蚕得所欲,日置他财,使人暴富。然遣之极难,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倍其所致金银锦物,置蚕于中,投之路旁。人偶收入,蚕随以往,谓之‘嫁金蚕’。不然能入人腹,残啮肠胃,完然而出,如尸虫也。有人守福清,民讼金蚕毒,治求不得。或令取两刺猬,入其家捕之必获,猬果于榻下墙隙擒出。夫金蚕甚毒,若有鬼神,而猬能制之何耶?”
在这一则想象中,金蚕始于四川,金蚕食蜀锦——而不是桑树叶(但是对桑蚕的经验可以提供类比联想)——是对人类财富的一种毁灭,在道德上具有恶的意义。金蚕毒毒死人后他人之财如何落入畜养者之手,这里的想象还没有注意道这个漏洞。大约沿袭《隋书》的说法,因为《隋书》也没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毒死人了,总要有回报吧,所以“使人暴富”。真正体现金蚕特征的是“水火兵刃不能害”这种生物也神奇啦!物理性的伤害对于它是没有作用的。必须用金钱才能摆平它,“必倍其所致金银锦物,置蚕于中,投之路旁”。 “金银天然是货币”,但是金蚕并不需要人类的货币。击败神奇的金蚕,除了金钱万能以外,还可以一物降一物。不起眼的刺猬便可以轻松地担当拯救世界的英雄。这与中国古代汉文化中相生相克的思维观念是分不开的。 金蚕蛊实际上是一则关于金钱和财富的道德论说。蜀锦在三国时期就“行销魏吴”,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蜀人与蜀锦的关系也就被密切化。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江南的丝织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当有人暴富的时候,以什么来解释这种成功呢,那就是他暴富的手段是不道德的。他用不道德的手段掠夺他人的财富,才是这个人暴富起来。他的这种手段最终还是很容易被打败的,这只需要一只小刺猬就可以了。正是由于怀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因而宋代也有吞食金蚕而不死的传说。《幕府燕闲录》中载有:“门良归告妻云:吾事之不可,送之家贫,何以为生?遂吞之,家人谓其必死,寂无所苦,竟以寿终,岂至诚之盛,妖不胜正耶?这里明白地表明了“妖不胜正”。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是千百年来流传的故事模式。" 但是对于“巫蛊”想象的制造最有功绩的是宋朝洪迈。洪迈的《夷坚志》多大420卷,现存206卷,记述鬼神怪异之事。“好奇尚异”的习性,[21]使得洪迈怎能放过“巫蛊”这一奇异而且便于发挥想象的优秀题材呢!他记述如下:
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雄雌,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一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雄雌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戚宗党, 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绍先母黄氏遭毒,垂尽,其家人曰:“若是中蛊,当烧床箦照之,必能自言。”黄氏遂云:“某年月日,为黄谷妻赖氏于某物内置毒食我,其所事之神,今尚在谷房里厨中。”绍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开厨,得银珂锁子、五色线环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针两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无眼,率非寻常人家所用。既告官,捕谷,讯鞠则佯死,释之则苏,类有鬼相助。会稽余靖为主簿,府帖委治此狱,其奸态如在县时。靖无以为计,惧其幸免,不胜愤呵,系于庭下, 砺刀断其首,贮以竹篮,持诣府自劾。府帅陈魏公具以状闻,诏提点刑狱谢师稷究实,谢与丞尉亲到谷家,蜈蚣甚大,出现,谢曰:“此明证也。摄赖氏还司自临考之。”三日狱具,亦论死。所谓顺逆棋子者,降虫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针之无眼者,以眼承药,既用则去之,盖所杀十一人矣。五色线,凡虫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银珂锁者,欲嫁祸移诸他处,置道旁,冀见者取之也。
宋代巫蛊传说非常盛行。其中福建地区蛊毒传说尤为显著。宋代的福建地区也不再是遥远的边陲,甚至有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福建一些地区巫术昌盛,巫者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对当地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22]巫者可以利用人们对于巫蛊的恐惧牟利。另一方面,福建地区由中原和山东移民而去的人很多。对土地、水源的争夺常常引发宗族械斗,族群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交织在一起。联系紧密的他者往往是竞争对手。巫蛊指控也成为当地民间一种用以排斥他者的手段。除了民间的口头相传,文学作品也在倾销巫蛊想象。宋朝的志怪小说产量也是很大的,“从数量上说,宋人志怪传奇不算少,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与唐人旗鼓相当,一点也不落后。”[23]洪迈的《夷坚志》就是代表。 元代,巫蛊记载的地域发生变化,逐渐走向华夏边缘。《元一统志》载清湘(今广西全州)“峒、僚错居其壤。山有毒蛇,储之为蛊以中人,立死。”[24]广西被纳入想象和指控的地域之中。而且与少数民族发生了联系,“峒、僚错居其壤”。这一方面是由于汉人南迁,更多地与少数民族接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这些地方自然环境特征的放大想象有关。元代还有“采生蛊毒”的巫术,但是与我们这里谈论的蛊毒不同。 _ 明代,这种对巫蛊的指控继续与福建相关,此外广西、甘肃、湖南、贵州、云南等帝国边缘都有此传说和指控。这些传说、谣言在对制造蛊毒的方法,防范的措施,甄别蛊毒的技术等都基本上继承了前代的说法,只是在具体记述时有一些调整和修改。例如,《汀州府志》记载,
“赖子俊廖高蒲皆上杭人,翁婿也。子俊传其妇翁张德之术,于每年端午采取百般毒虫,封贮瓦子罐,自相吞食,逾年启视,犹有一虫,形如蚕,色如金,取三四片茶叶、枫香养之,择日占断,一年当用几次依占取出虫粪,秘置饮食中,使人腹痛,死后魂魄为之力作,坐是致富。翁婿递相承受,逢朔望日,夫妇赤身拜祝云:‘金蚕公,金蚕娘,我家夫妇没衣裳’等语。”
但是就是这样,也有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首先,金蚕的食物从蜀锦转成了茶叶、枫香。蜀锦对于当地已经不在重要。其次,歹人致富的具体手段在于被害死的魂魄被歹人驱使。这就补足了原来想象中的明显漏洞。最后,“翁婿相承”的说法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今天关于蛊毒的传说,已经转向母女相承。在今天的传说中,如果娶“有蛊”家的女人,丈夫也会变得有蛊。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多有治蛊之方,但是其中巫术色彩浓郁。与孙思邈一样,李时珍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对“蛊”的治疗交付巫术。中医对“蛊”疾一直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疾病内容来对待。相关的疾病被中医诊断为蛊疾,并有一套治疗之法。这种疾病划分为人们将巫蛊视作真实疾病原因提供了基础。
简单梳理,许多重要的内容可能被遗漏掉了,而且对于历史上巫蛊论说也不是本文可以完成的任务。但是,梳理文献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对“巫蛊”的想象如何在推测疾病原因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被最终建立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视为“史实”。在这一过程中,巫术和巫术思想作为这种想象的外部土壤,为其提供了精神空间。自然疾病的存在则是这种想象得以生根发芽的依附点。佛教和道教影响下汉人社会的鬼神观念与志怪小说的融合逐步衍生出一种魔幻的、恐怖的“巫蛊”传说。当这种传说从杂史走入正史,关于畜养蛊虫的巫术指控在相当程度上也为官方接受以后,民众不自觉地受到这种巫蛊想象。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各朝代的巫蛊想象有明显的前后相承关系;但是,也有各朝代各自不同的特点。它反映了中华帝国的边疆南移的过程中,族群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社会冲突的一面。
明清之前的巫蛊想象和指控很少发生在西南地方,也鲜见关于苗人放蛊的说法。明清以后,关于苗人或少数民族放蛊的说法多了起来,并在西南地区形成了惟苗人或少数民族放蛊的传说。* 《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8)巫蛊故事的基本定型》由我要咒语网资料整理与编写,转摘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