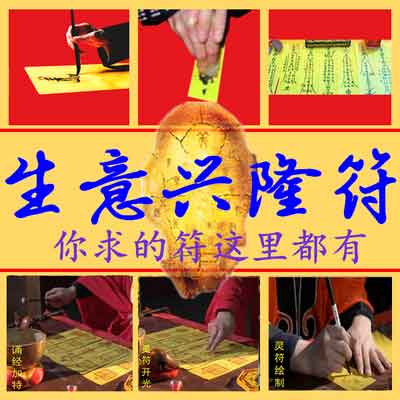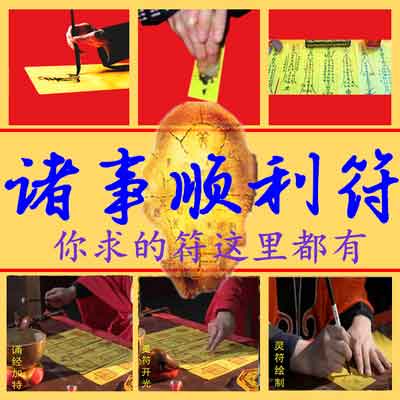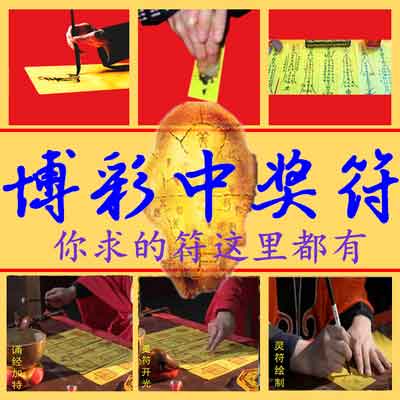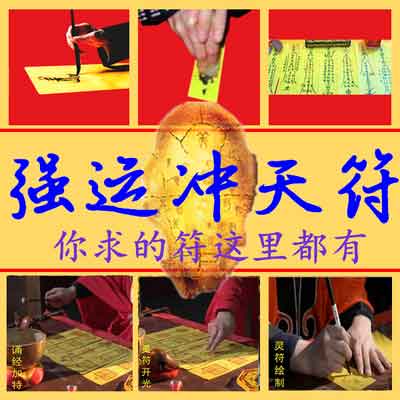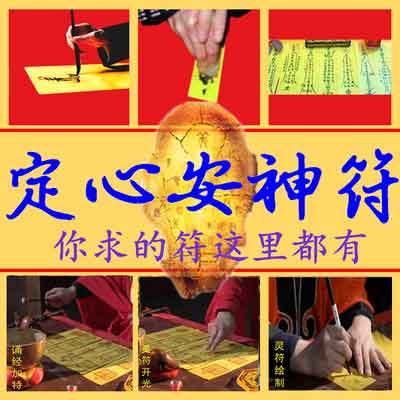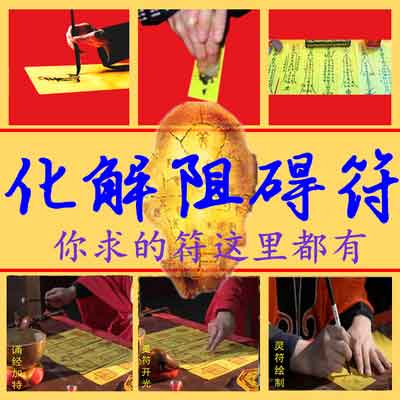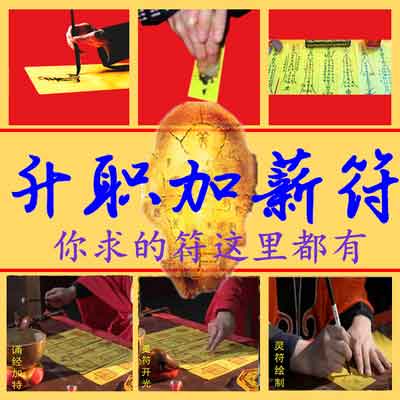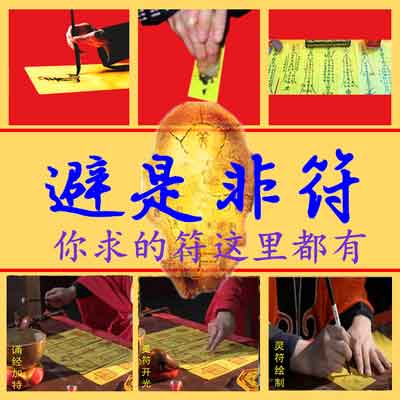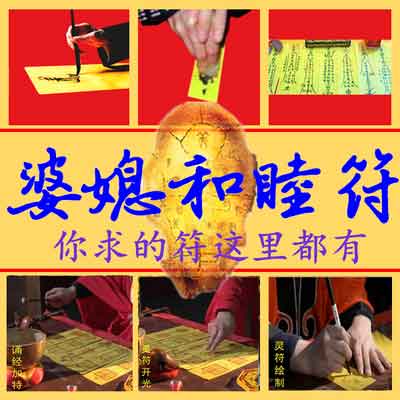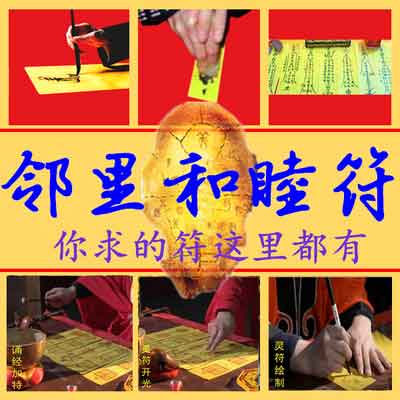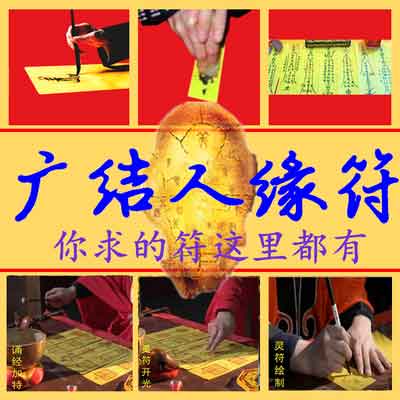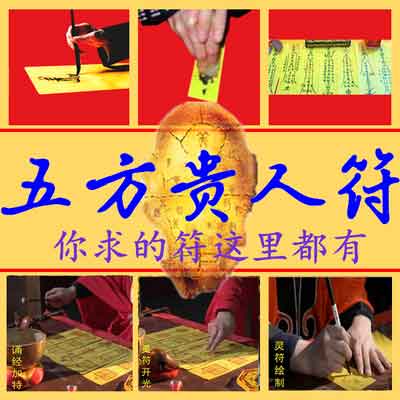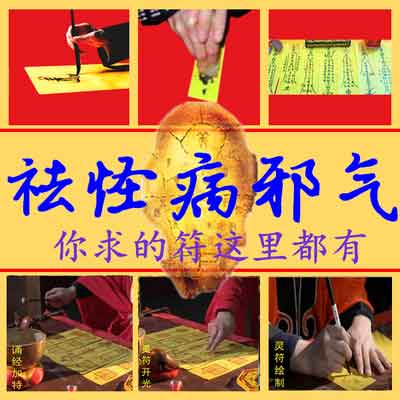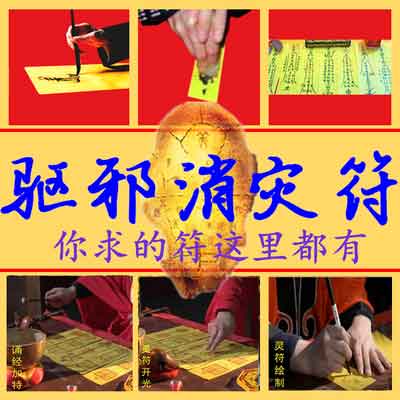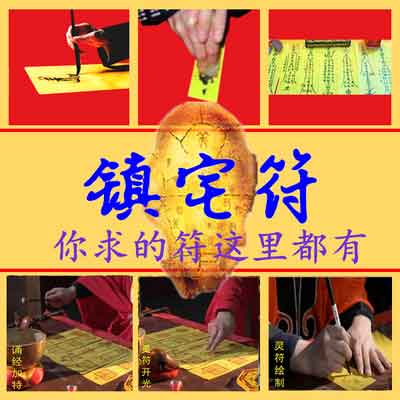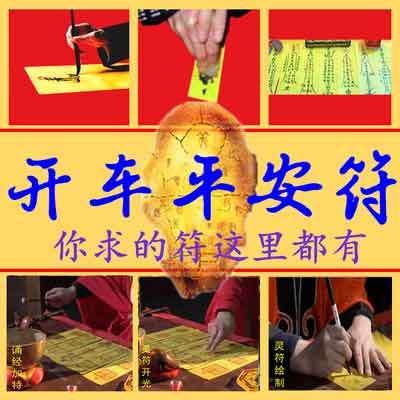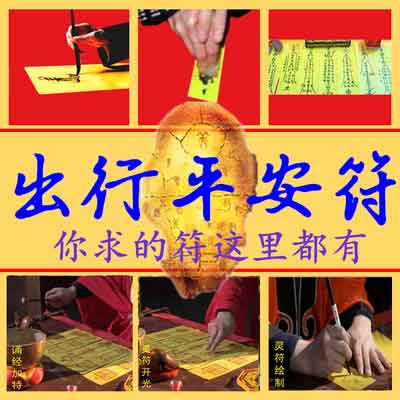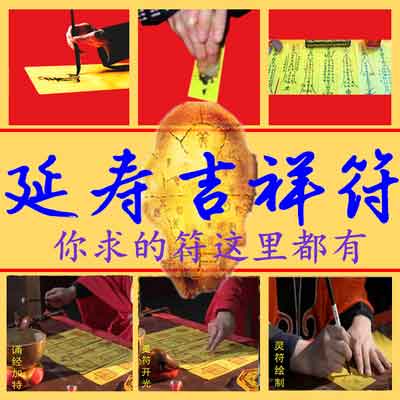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4)巫与巫术
“巫蛊”是本文所谈及的主要内容。西汉“巫蛊之祸”早已被历史学家关注。由于“巫蛊”比“蛊”更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本文的题目使用了“巫蛊”的说法。但是,在这里“巫”与“蛊”被认为是不同的。之所以这么做,在于这种划分直接与本文的中心议题相关。只有对“巫”与“蛊”进行恰当的划分,才能使本文所讨论的概念有一个比较清晰、可进行操作的基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与“蛊”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与“巫”有关的问题。当然,题目使用了“巫蛊”的说法,说明“巫”与“蛊”具有紧密的关系。
巫是古代能够通神的人,舞蹈是他们用以通神的手段。“巫”在《辞源》上的解释是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
《国语·楚语下》说,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日巫。
可见巫者是司神之官,是智圣聪明之人,具有通神降神的本领。《墨子·非乐》引《汤之官刑》有“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的说法。由此可见,“巫”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唱起来一定非常疯狂。《说文解字》卷五“巫,祝也,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义。”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南邹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现作乐歌以娱神。”
巫师们不仅以舞降神,而且连降神的步伐也被神化,用以提高社会地位。
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此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程其事。或有伏泉磐石,非眼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祗向以决之。然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行,令之人术。自兹以还,无术不验。因禹制作,故是禹步。(《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1]
胡新生对此论述到,
“春秋以来,大批跛者加入到‘以舞降神’的巫师行列。随着跛巫群体的发展,巫术舞中‘步不相过’的蹇跛步法逐渐为众多术士所认同。惯于假托的战国术士宣称这种巫术舞步出自夏禹,并将其命名为‘禹步’。从此,禹步即被所有术士奉为经典性的基本步法,且对宗教、巫术等仪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神化跛步、确立‘禹步’名称方面,迷信巫术和崇拜夏禹的墨家学派曾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润作用。”[2]
巫者不仅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也参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中国古代的巫者通常的职能包括以歌舞事神,职掌交通鬼神(即以祭祀、占卜与预言、祈禳、驱邪避鬼、招魂等活动而祈求福祥与避免灾祸)、医疗病患、灾祸之事(即包括旱灾、风雨、蝗灾、战灾等)、生产活动、神明裁判之事、祝诅放蛊之事、求子生育、建筑之事、丧葬之事等。[3]巫者具有会通人神,制订规范,创造艺术,传播文化,联接历史的功能。巫是上古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传者。[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巫’和‘巫’的影响存在,但这种影响从很早就被限制,不再具有支配地位。” [5]这种限制既有对黑巫术的恐惧,也有对巫者干预政治的担心。
总的看来,古时的巫以舞降神,他们很多是女性,还很有可能有不少残疾人。他们时常表现出癫狂的精神状态,被其他人视为智能超常的人。这些与萨满十分相似,而萨满则是通古斯语族的“巫”,萨满的本义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由巫者的职能,及其在社会上所展现与民众生活依存的关系,可以分析巫者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巫术能助人类应付生活上所遇的挑战与危机,甚至包括恐惧鬼神、精灵以及黑巫术所带的威胁。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民众生活仍然存着困难与危机,巫者便有活动的空间。
对巫有所了解之后,应当对巫术也有一个界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以线性进化的方式来看待巫术。他认为巫术阶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级阶段。
“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人类的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人类的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这是我们理解魔法的关键。人早在低级智力状态中就学会了在思想中把那些他发现了彼此间的实际联系的事物结合起来。但是,以后他就曲解了这种联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联想当然是以实际上的同样联系为前提的。以此为指导,他就力图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而这种方法,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具有纯幻想的性质。根据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生活中广泛众多的事实,可以鲜明地按痕迹探求魔法术的发展:其起因是把想象的联系跟现实的联系错误地混同起来;从它们兴起的那种低级文化到保留了它们的那种高级文化。”[6]
对于巫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人类学家弗雷泽。他区分了巫术思维的两个基础:一个是“相似律”,一个是“接触律”。弗雷泽指出巫术思想原则虽然有错误,但是它出于原始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思考。他说:
总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之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民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之为‘应用巫术’。”
弗雷泽的巫术理论对于促进20世纪初中国本土巫术研究的开展影响重大,与之相关的论著如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郑振铎的《汤祷篇》、江绍原的《发须爪》等等。梁钊韬1940年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则是将弗雷泽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史前巫术的一种尝试。弗雷泽开创性的成果引起了激烈的讨论。[7]
马林诺夫斯基说,
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一切人生重要趣意而不为正常的理性努力所控制者,则在一切事物一切过程上,都自开天辟地以来便以巫术为主要的伴随物了。[8]
《苏联大百科全书》概括为:“巫术是一种附有信仰的仪式,即相信人能通过超自然的途径对他人、动物、自然现象,以及想象中的鬼神产生影响。”
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中说,
巫术(magic)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历史各阶段的宗教现象。它的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9]
张紫晨在《中国巫术》中说,
巫术,在国际上用Magic来表示,在中国则以‘做法’或法术相称。国际上已把巫术的活动、做法上升为学术术语,并赋予它以科学的概念。巫术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基础上,出于控制事物的企图而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 [10]
《中国百科大辞典·人类学》说巫术是
原始宗教的形态之一,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人相信巫师的巫术具有支配超自然力的能力,并能借此对客体施加影响。例如通过击法鼓、跳神舞等方法驱使鬼神,并以唱歌的形式传通鬼神的意态,替人治病、占卜、消灾、降幅。曾普遍流行于世界的许多民族之中。
尽管巫术可以是非理性认识的行为。但是,一般认为巫术要通过某种仪式或活动来完成,它是一种带有明确意图的实践行为。仪式或者某种特定的活动是巫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白巫术,还是黑巫术,都有现实形态,都可以设法观察。无论什么类型的巫术总是有一定现实形态。 《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4)巫与巫术》由我要咒语网资料整理与编写,转摘请注明出处。
巫是古代能够通神的人,舞蹈是他们用以通神的手段。“巫”在《辞源》上的解释是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
《国语·楚语下》说,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日巫。
可见巫者是司神之官,是智圣聪明之人,具有通神降神的本领。《墨子·非乐》引《汤之官刑》有“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的说法。由此可见,“巫”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唱起来一定非常疯狂。《说文解字》卷五“巫,祝也,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义。”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南邹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现作乐歌以娱神。”
巫师们不仅以舞降神,而且连降神的步伐也被神化,用以提高社会地位。
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此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程其事。或有伏泉磐石,非眼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祗向以决之。然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行,令之人术。自兹以还,无术不验。因禹制作,故是禹步。(《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1]
胡新生对此论述到,
“春秋以来,大批跛者加入到‘以舞降神’的巫师行列。随着跛巫群体的发展,巫术舞中‘步不相过’的蹇跛步法逐渐为众多术士所认同。惯于假托的战国术士宣称这种巫术舞步出自夏禹,并将其命名为‘禹步’。从此,禹步即被所有术士奉为经典性的基本步法,且对宗教、巫术等仪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神化跛步、确立‘禹步’名称方面,迷信巫术和崇拜夏禹的墨家学派曾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润作用。”[2]
巫者不仅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也参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中国古代的巫者通常的职能包括以歌舞事神,职掌交通鬼神(即以祭祀、占卜与预言、祈禳、驱邪避鬼、招魂等活动而祈求福祥与避免灾祸)、医疗病患、灾祸之事(即包括旱灾、风雨、蝗灾、战灾等)、生产活动、神明裁判之事、祝诅放蛊之事、求子生育、建筑之事、丧葬之事等。[3]巫者具有会通人神,制订规范,创造艺术,传播文化,联接历史的功能。巫是上古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传者。[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巫’和‘巫’的影响存在,但这种影响从很早就被限制,不再具有支配地位。” [5]这种限制既有对黑巫术的恐惧,也有对巫者干预政治的担心。
总的看来,古时的巫以舞降神,他们很多是女性,还很有可能有不少残疾人。他们时常表现出癫狂的精神状态,被其他人视为智能超常的人。这些与萨满十分相似,而萨满则是通古斯语族的“巫”,萨满的本义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由巫者的职能,及其在社会上所展现与民众生活依存的关系,可以分析巫者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巫术能助人类应付生活上所遇的挑战与危机,甚至包括恐惧鬼神、精灵以及黑巫术所带的威胁。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民众生活仍然存着困难与危机,巫者便有活动的空间。
对巫有所了解之后,应当对巫术也有一个界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以线性进化的方式来看待巫术。他认为巫术阶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级阶段。
“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人类的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人类的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这是我们理解魔法的关键。人早在低级智力状态中就学会了在思想中把那些他发现了彼此间的实际联系的事物结合起来。但是,以后他就曲解了这种联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联想当然是以实际上的同样联系为前提的。以此为指导,他就力图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而这种方法,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具有纯幻想的性质。根据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生活中广泛众多的事实,可以鲜明地按痕迹探求魔法术的发展:其起因是把想象的联系跟现实的联系错误地混同起来;从它们兴起的那种低级文化到保留了它们的那种高级文化。”[6]
对于巫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人类学家弗雷泽。他区分了巫术思维的两个基础:一个是“相似律”,一个是“接触律”。弗雷泽指出巫术思想原则虽然有错误,但是它出于原始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思考。他说:
总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之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民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之为‘应用巫术’。”
弗雷泽的巫术理论对于促进20世纪初中国本土巫术研究的开展影响重大,与之相关的论著如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郑振铎的《汤祷篇》、江绍原的《发须爪》等等。梁钊韬1940年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则是将弗雷泽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史前巫术的一种尝试。弗雷泽开创性的成果引起了激烈的讨论。[7]
马林诺夫斯基说,
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一切人生重要趣意而不为正常的理性努力所控制者,则在一切事物一切过程上,都自开天辟地以来便以巫术为主要的伴随物了。[8]
《苏联大百科全书》概括为:“巫术是一种附有信仰的仪式,即相信人能通过超自然的途径对他人、动物、自然现象,以及想象中的鬼神产生影响。”
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中说,
巫术(magic)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历史各阶段的宗教现象。它的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9]
张紫晨在《中国巫术》中说,
巫术,在国际上用Magic来表示,在中国则以‘做法’或法术相称。国际上已把巫术的活动、做法上升为学术术语,并赋予它以科学的概念。巫术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基础上,出于控制事物的企图而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 [10]
《中国百科大辞典·人类学》说巫术是
原始宗教的形态之一,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人相信巫师的巫术具有支配超自然力的能力,并能借此对客体施加影响。例如通过击法鼓、跳神舞等方法驱使鬼神,并以唱歌的形式传通鬼神的意态,替人治病、占卜、消灾、降幅。曾普遍流行于世界的许多民族之中。
尽管巫术可以是非理性认识的行为。但是,一般认为巫术要通过某种仪式或活动来完成,它是一种带有明确意图的实践行为。仪式或者某种特定的活动是巫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白巫术,还是黑巫术,都有现实形态,都可以设法观察。无论什么类型的巫术总是有一定现实形态。 《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4)巫与巫术》由我要咒语网资料整理与编写,转摘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