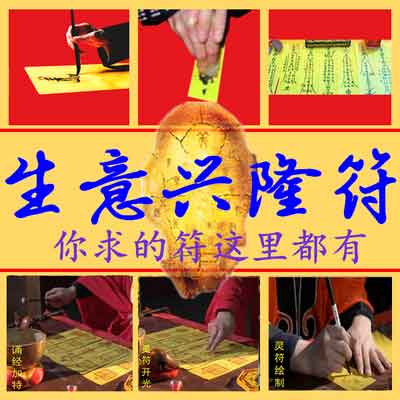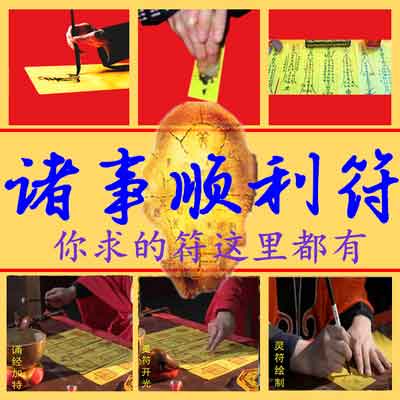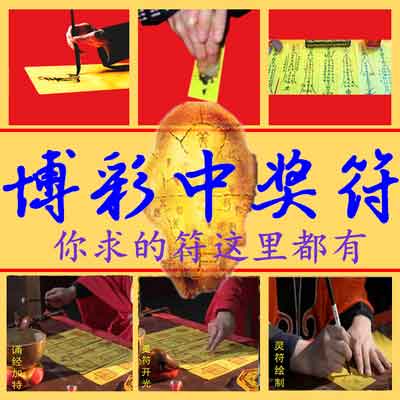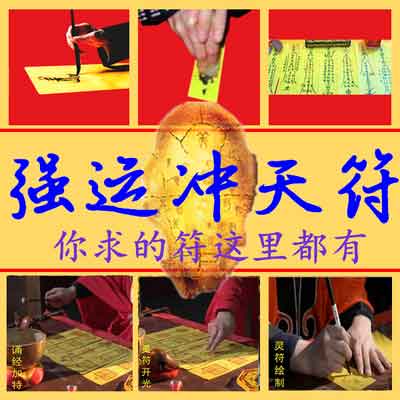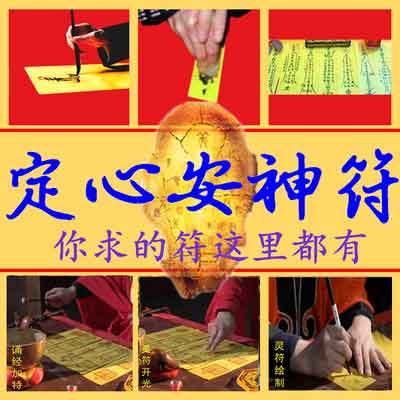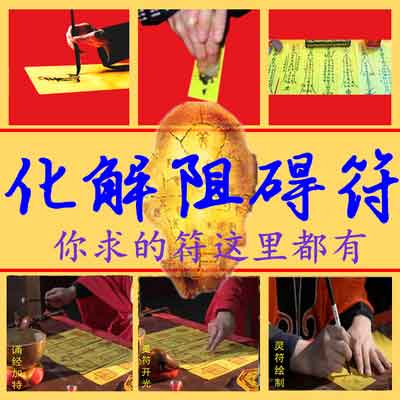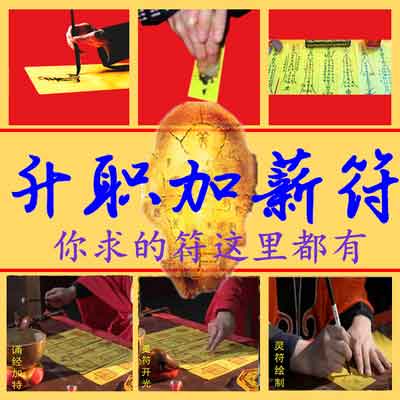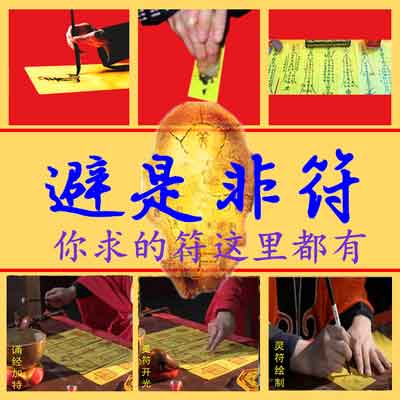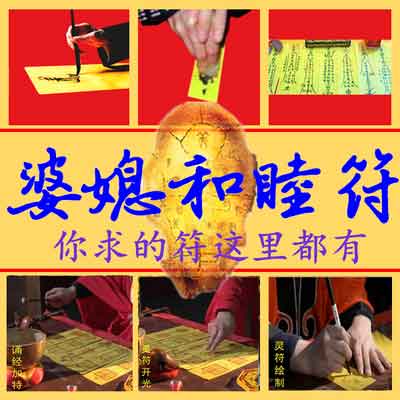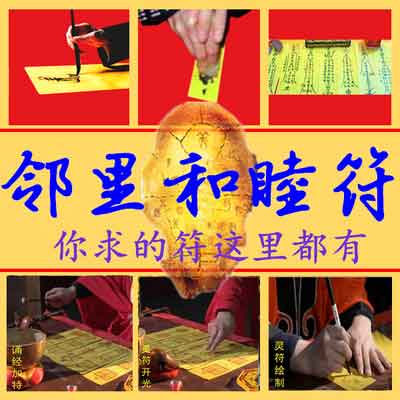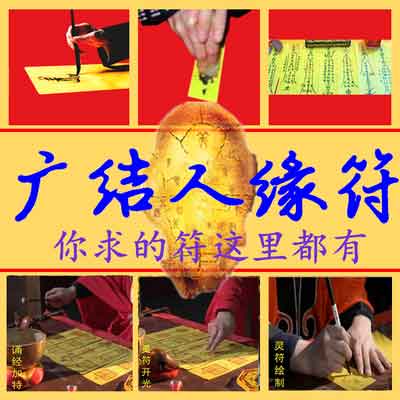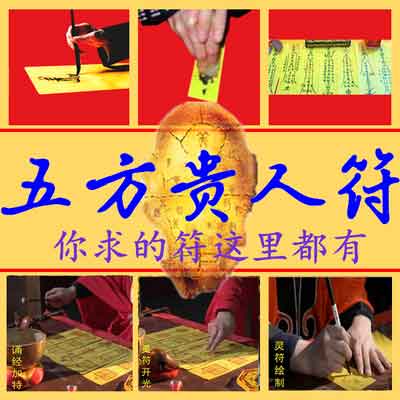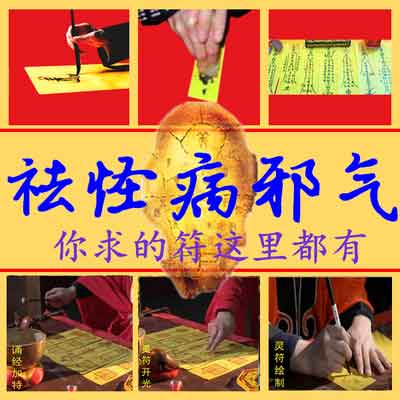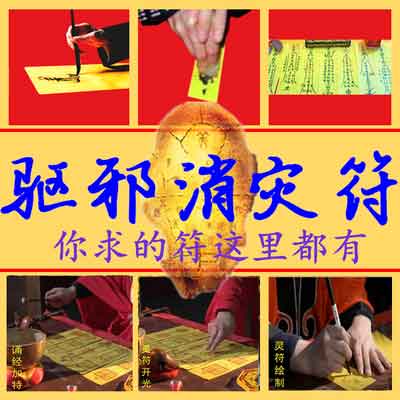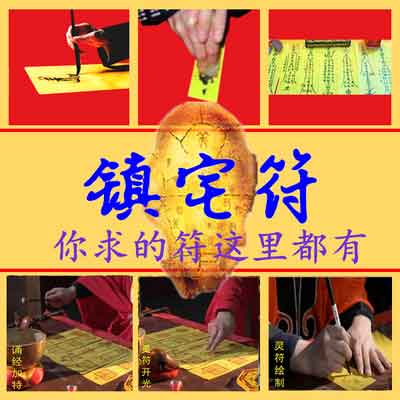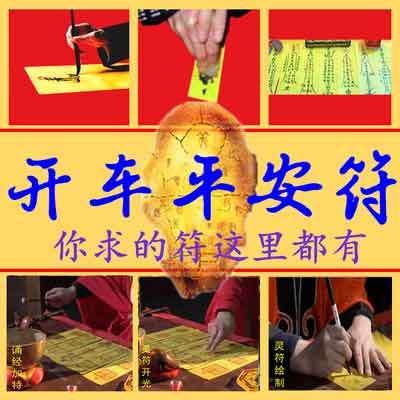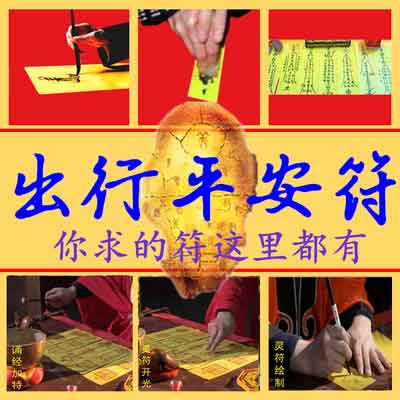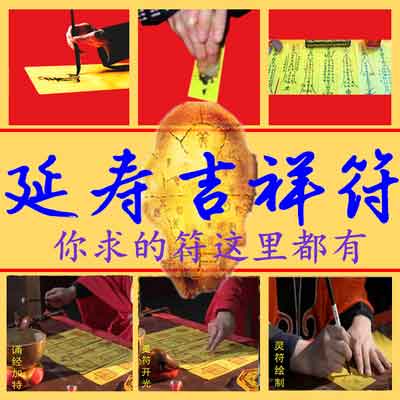宗教对养老的影响与参与
天增岁月人增寿,新年过后,每个人又成长了一岁。对于那些年寿已高的老人来说,增加一岁也意味着养老问题的迫近。事实上,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要面临出生率降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新态势。当老龄化社会到来时,一个国家不仅需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难题,还要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为老人提供合适的赡养保障方式。
在以家庭为生产团队的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的赡养主要靠家庭承担。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力高速发展,经济日益繁荣,物产日趋丰富,服务性行业和部门日渐增多,这些都为老年人的赡养由家庭转向社会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家庭的养老功能随之降低。除了经济因素外,宗教因素对于养老制度的选择和变化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养老伦理受到宗教传统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推行了一整套社会养老措施,使国家与社会承担起养老的重任,这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及基督教的自助、互助精神不无关系。基督教宣扬的孝与爱是一种无差别的神圣之爱,这种神圣之爱讲究爱人如己,没有父母兄弟与邻居远亲之别。其最重要的不在于血缘关系和亲疏远近,而在于是否敬仰共同的神。在这种宗教观念的熏染下,亲密的感情来自于共同的信仰,而不是源于血缘宗族。
相比之下,中国的养老传统则以孝道思想为基石。在儒家看来,爱的感情以血缘的远近为依据,亲疏有别。在这种道德伦理的影响下,赡养父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儒家强调并推崇孝道,其基础都是以直接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而扩展延伸开去,形成一种尊老文化,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赡养父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在养老模式上也就选择了家庭养老,由子女承担物质赡养和心理敬养的义务。
其次,养老救济得到宗教组织的支持。对于那些没有子女赡养的老人,就需要有社会机构来承担。在古代瑞典,有一种作用于社会养老的仁杖制度。在村镇长者的监管下,一根长约1米的方形木杖按户传递,传至谁家,谁家就有对邻居的老弱贫病者给予扶助、照顾的义务。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各类自愿互助组织以及私人保险、政府救助都在对老年人实施的经济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01年,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基督教区负责向老人、病人和贫穷儿童提供救济。17至18世纪,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仿效此法。基督教会对老人的救济既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爱,也促进了社会救济向社会养老的过渡,推动了养老社会化的发展。
再次,养老机构获得宗教力量的参与。虽然政府承担了兴办养老机构的重要责任,但在许多贫困偏远地区,仍需要宗教力量提供补充性的养老活动。目前,基督教在福建全省范围内已经办起了8所养老院,其中福州4家、南平1家、厦门1家、莆田2家,基督徒们在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时有爱心、有耐心,服务周到,为社会养老分担了一份责任。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普法法师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大力引导宗教界融入社会参与兴办养老事业》的提案。在提案中,普法法师写道:(佛教界)应积极参与兴办养老公益事业,建设以老人赡养为主的专业养老机构,使老有所养、老有所学、病有所医、死有所安。
据预测,进入21世纪中叶以后,我国的老年问题将成为社会最关注,也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宗教组织也将具有更多发挥作用的渠道,为满足老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需要提供多样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