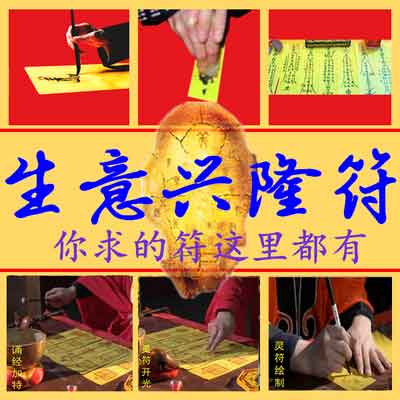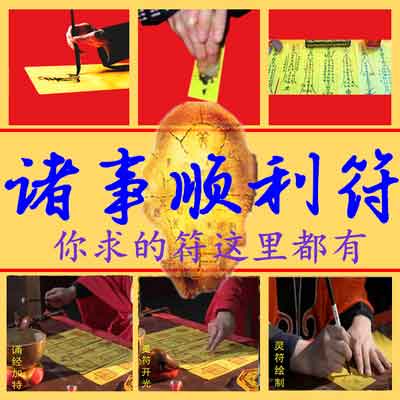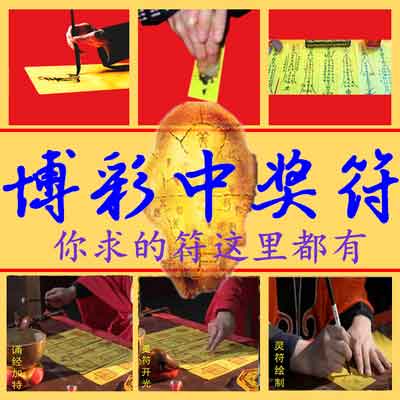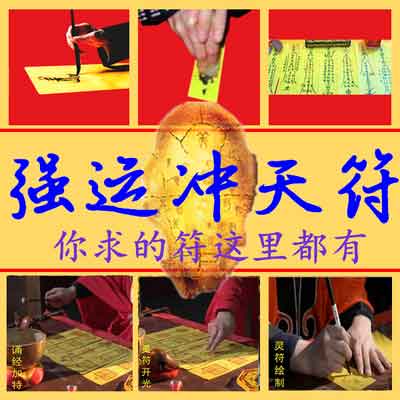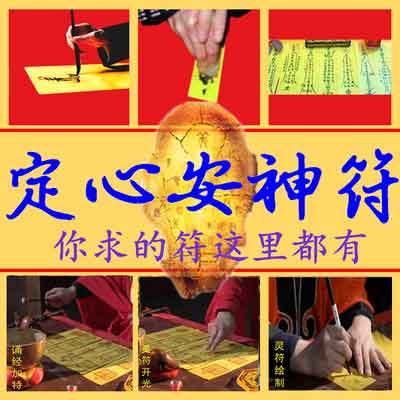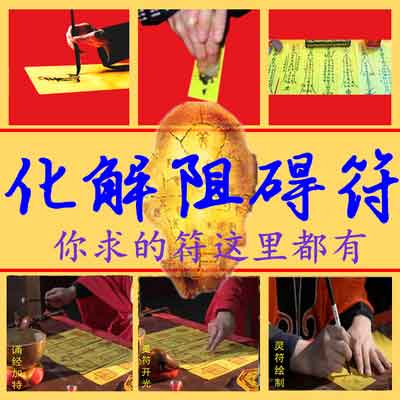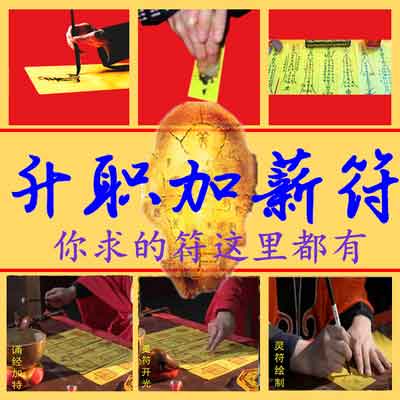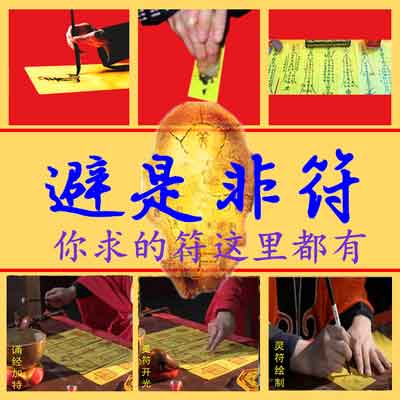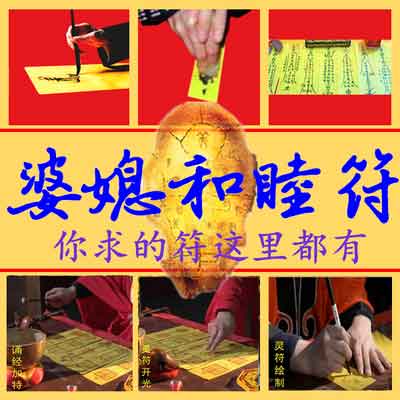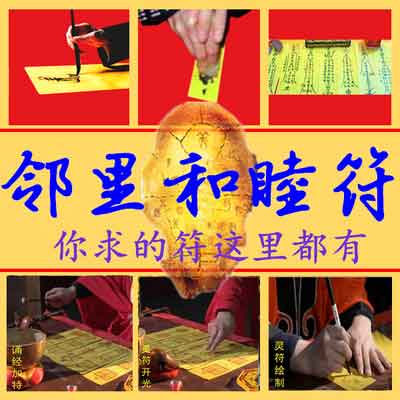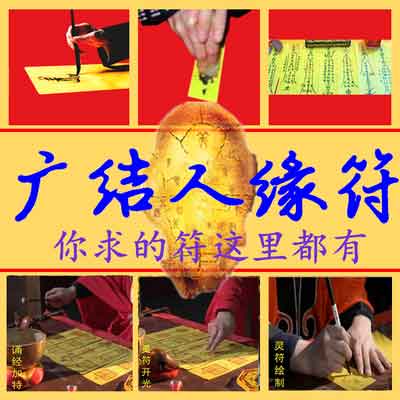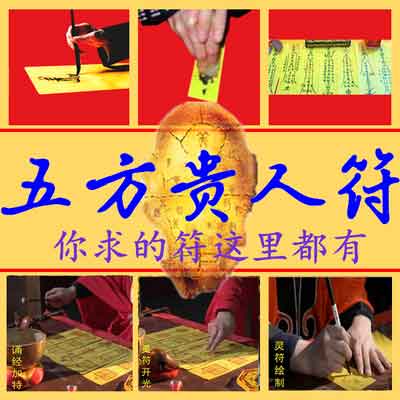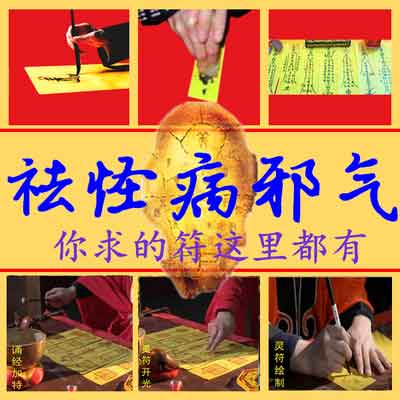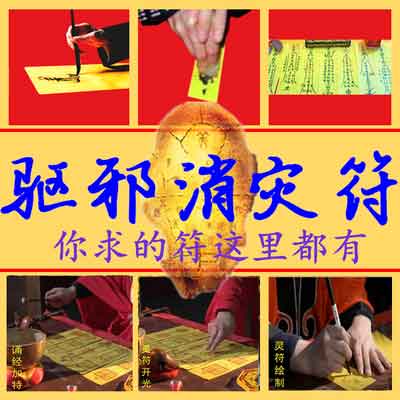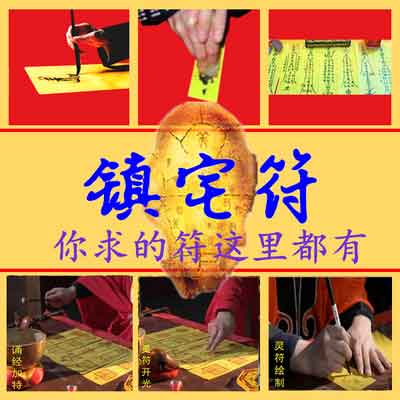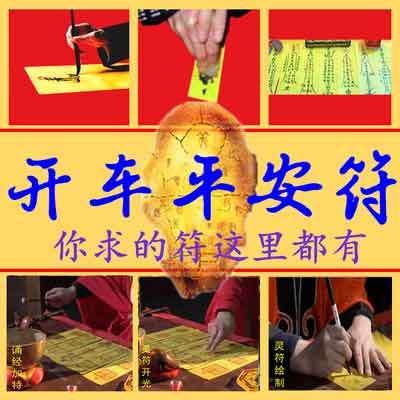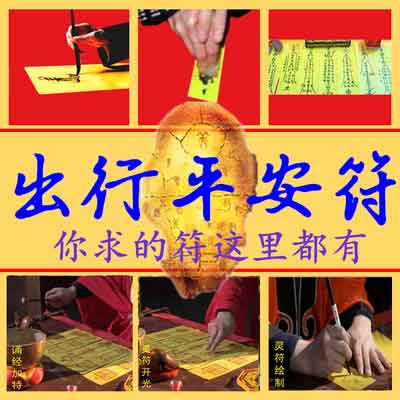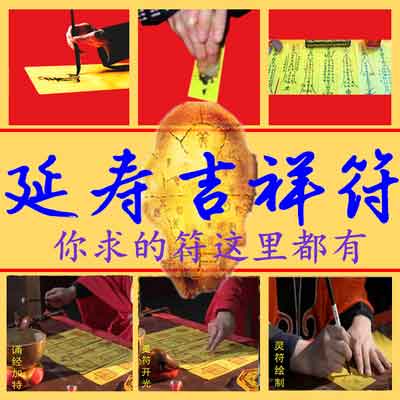国际学者探讨当前道教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腾讯道学岳阳讯(妙眼)7月31日上午,首届国际道教文化前沿论坛在结束了两天的会议日程后进入到最后的总结阶段。会场分为两部分,分别由学者与道教界代表参加。美国罗格斯大学刘迅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分别主持了两个会场的讨论。
圆桌会议:当前道教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出版计划
在由刘迅教授主持的“圆桌会议:当前道教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出版计划”中,几位领谈人先发表了看法。
刘迅教授主持国际学者探讨“当前道教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出版计划”(朱伟民摄)
“道教研究的范围有待拓展”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柏夷教授说,我看到众多学界的老朋友已经将原来的研究扩大、或进入新的领域,尤其是李福教授和刘屹教授在佛道关系的研究上已经旁开眼界,吴真教授和戴文琛教授从道教文学艺术角度的研究也让我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学者来自不同角度研究的声音。
柏夷教授(朱伟民摄)
谨慎使用所谓“学术概念”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祁泰履教授在总结中再一次讨论了发表时所提的学术“概念”问题,他说我们用概念需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用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宗教和哲学。祁泰履教授认为,宗教最核心的不一定是想法和意见,而很可能是仪式,我的很多西方朋友都采用这样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学者是否也能采用。他说,自己最开始研究道教是因为道教很多地方像早期西方天主教,但现在唯一能说得上是道教徒的只有道士,那么那些山里独修的、在家修行的能不能说是道教?我倾向于放在一点去研究,就是“live religion”,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它翻译为“活着的宗教”,而是译为“实践宗教”的原因。
“田野研究与历史文献研究应当更好的结合,绝不能离开经典”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王岗教授说,巫能昌博士(复旦大学)、潘君亮博士(法国丹尼斯狄德罗大学)的田野功夫非常扎实,刘迅教授和洪怡莎(Isabelle Ang)教授(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则将田野与历史结合得非常好,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很尊重他们的研究。但我还是要强调“有文献背景的田野考察”。西方有部分研究对文字有排斥,这在中国行不通,尤其道教是文字的宗教。我呼吁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研究,都不能缺少对历史的了解,这是我所学到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志添教授在发言中回忆道教学发展历程,道教研究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主要以历史和经典研究为方法和对象。现在,随着方志的出现和对田野、口述历史、艺术、文学等等方面的重视,大家已经把视野和方法扩展到了经典之外,将不同的学科和手段结合起来,这很值得高兴。但是经典是不能离开的,否则道教的身份就不能被揭示出来。
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朱伟民摄)
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也强调道教研究不能离开经典,他说,也许外国学者可以,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能。另外,有更大量的资料在文集中,将来还要多做文集方面的工作。
四川社科院李远国教授在认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道教研究若拘于文献则难有创新,出不了新的学术成果,只能是“炒饭”。同时应当重视对图像的研究,经典的文字难以理解,但如果有对应的图像就一目了然。
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强调了对道教基础文献研究的部分。他说,道教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有差别,历史研究也许从史料拿出的结论更加直观,但道教方面刘教授发问道:我们对道藏的研究够了吗?他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和成果与道藏这个大的资料库相比可能还相差很远,例如《道法会元》,我们还有很多没了解到的东西。所以在重视新资料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旧文本的研究。
“加强明清道教研究”
在历史部分上,黎志添教授希望加强明清道教的研究。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也强调了明清道教史的研究。他说,从乩坛到道坛是理解明清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的关键,清代方面已经有人做过乩坛地理分布的研究,但是明代方面还不甚了了,明以后道士分“住观”和“在家”,乩坛由在家的道士主持,不了解在家道士就不能理解明清道教。现在很多提法说,明清以后道教是衰落了,我们如果考虑到上述问题是否还能说明清后衰落?我觉得我们不能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从明清开始衰落这个框架来套用。
土屋昌明教授(朱伟民摄)
“道教研究的地域范围不应当局限于中国”
日本东京大学土屋昌明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道教研究文化学角度的地域范围问题。他说,王岗教授提到了“汉族的道教”,但其实道教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还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学界认为,应该表述的概念是“东亚世界”和“汉字文化圈”,在这个范围中道教是重要的部分。同时,日本文化中道教的因素也不能忽视,道教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不是作为独立的道教,而是在佛教、神道教、道教美术中融合的道教,前一段时间一个相关的展会上展出的很多藏品都是日本收藏的。土屋教授说,我希望大家能扩大视野,道教是东亚共同的。刘迅教授总结时对此方向表示认同,他说,我们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也要看到道教的“广地域性”,道教即使不是“世界性”,也是“广地域”的。大家一直都把鲁迅的那句“中国的根柢在道教”记得牢牢的,但其实我们不必拘泥于此。
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也提及了道教与国际社会的问题。她说,我在国外做的“道学西用”课题中看到道学已经在西方得到了很多应用,例如有一本《Tao of the leadship》在某个数据中的援引次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多次。吕教授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道学在西方的影响力,她说,我们不仅要研究道教本身,还要宽阔视野,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人类做贡献。
“道教的发展、教义的变化值得重视”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固盛教授说,他同意何建明教授所提命题的前半句:道教的精神主旨在《道德经》中,但是主旨是否是“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还可以讨论。《道德经》与道教的发展、教义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
“建立公用道教大数据库的若干问题”
黎志添教授提出应当建立既保全个人的努力、又可供大家利用的大数据。一个学科的发展若是没有大数据的话发展很难,如果一个学科的数据资料不能代表这个学科,那么作为这个学科是应该感到惭愧的。黎教授带头说,自己已经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有的明清资料扫描上传。他说,与我们合作的道士信任我们才让我们给他们的资料拍照,我们要把我们做的还给道教,否则对道教的谱系是不公平的。
对于黎志添教授提出的建立数据库的问题,学者们又进行了很多讨论。柏夷教授对数据库的作用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举例说,北京大学做的基督教信仰研究数据显示,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县镇GDP也随着提高,这与每个去基督教教堂信仰者的登记有关,但道教和基督教是不同的宗教,这边的情况是也许今天拜道教的神明天拜佛教的神,那么我们的数据表明的是什么?数据很可能是不足为信的,所以我们应该谨慎使用数据。
会议发表中,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教授的论文与数据库问题有关,刘迅教授请付海晏教授回应,付教授同样指出了数据库的几个问题。他说,关于量化,我们也许非专业,数据也有被庸俗化的可能,且首先也许一些基本事实层面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在中国,这一层面我们有时很难得到一些基本事实的认识;在政府管理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问题和界定,我想自己的研究会今后在这个层面做一些努力。
澳门大学白照杰博士则提供了国际上道教学术数据库的最新消息。他说据了解,接下来的八年,哥伦比亚大学正在筹划做这样的数据库,所有的经书和八年间的田野资料都要收入,并请专业机构操作,会免费对个人开放,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样貌。
“进行学科建设,关注公共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教授提出,我们很有必要回顾道教界的研究,并提出反思。道教界的学者可能比其他很多学科的学者忙,因为既要研究文本又要做田野,既要研究古代又要研究现代,既要关注中国又要关注外国,任务可能更重。我们有必要集中去回顾,总结到现在为止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后来的学者有更清晰的方向感。陈教授表示很同意黎志添教授的提议,认为我们应该进行学科建设,关注公共的问题。
李福教授在讨论中再次提到了方法论的问题。他说,“道教学”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门学科,因为它结合了非常多的学科门类与研究方法。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很少有道教研究方法论影响西方的方法论或别的理论。方法应该是国际的,但道教现在在这一部分还是空缺,希望这方面可以看到新的突破。
李福教授(朱伟民摄)
“加强实践性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赵建勇尖锐地指出了这次会议的不足,他说这次会议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地域、田野,但有七个方向都有空白,做任何研究第一步都应该是内史(技术史),但这次会议里面的法术研究几乎空白,我们需要加强实践性的研究,重要的不是认识,而是改变。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樊光春教授提出了对于“修炼”的界定问题。他说,在伊斯兰等宗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仿照道教修炼的部分和痕迹,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要怎样研究,要将它算在道教中吗?
“开放、可交流的道教研究”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谢聪辉教授则提出了非常新颖的概念:“道教+”。“+”表明的不仅是正向的能量,而且是开放的、可交流的、可以让别人容易进入的、影响更大的道教。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谢聪辉教授发言
南京大学杨德睿教授深刻地指出了道教研究与其他相关领域关系中潜藏的问题。他说,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也许没有和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因为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太过强大,设定了太高的门槛,其他很多人都进不来。我与很多研究民族学的人交流,他们关注的问题是:这群人怎么活。这些学者所做的研究,可以很抱歉地说,都跟道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样的怎么办。有的学者跟我说自己想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却发现所研究的问题根本不够用。有的说他们在道教学院中觉得最有用的一门课是宗教心理学,而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又基本来自西方基督教。那么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道教开端时间如何界定”
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提出的道教开端时间界定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他提问道,为什么昆仑山西王母不能作为道教的信仰而纳入道教历史,为什么要排斥?昆仑山可以说是 洞天福地背后的“总部”、“关节点”,汉代的画像砖和《真诰》都有相关证据,而这一部分现在做的很少,如果可以算作开端,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只写了半部道教史。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对此表达了反对的观点,他说,昆仑山西王母是公共的资源,昆仑观念也许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但见于史料的是在汉朝,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刘迅教授评论道,这个想法想象力很丰富,但我们还是要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道教研究与当代社会”
会议赞助方之一的敦和基金董事长熊敏华女士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了非常现实的问题。熊女士说,第一,通过这次会议我可以看到道教确实是文化的宗教;第二,我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当代问题、回到日常生活;第三,反思道教研究与其他领域比是否有前沿性;第四,我们关心的是学者们研究的这些问题是否与时俱进,对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有影响、是不是起作用、是否有贡献。
何建明教授总结发言(朱伟民摄)
何建明教授在学者们的讨论最后做了总结。何教授说,我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佛教,因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办的班上带一批道长、以及与道教学者们交流而萌生筹划这次会议的想法。会议上我们能看到各地学者的差异性,比如祁泰履教授认为道教的核心是科仪,但这在大陆学者中可能就没有多少认同感。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进行问题意识和方法的反思。现在道教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开始重视个案、田野、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的运用,我非常喜欢这些新方法,因为它们特别实在、能够解决问题。但其中一个缺陷是,能否通过道教研究提升形成对宗教学的启发。以后我们的会议也许不是讨论学者个人的课题,而是对学术史进行梳理,然后结合个人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进而影响宗教史。熊敏华董事长虽然不是做宗教研究的,但我们在聊天中我觉得她的想法与我非常一致,就是要关注学者研究的现实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我没有定主题的原因。如果能有对自己领域的方法反思,那么与大家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共通语言。我们要达到“共通”,而不是“共同”。以后我们可能会邀请更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样相信对他们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编辑:行云)
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