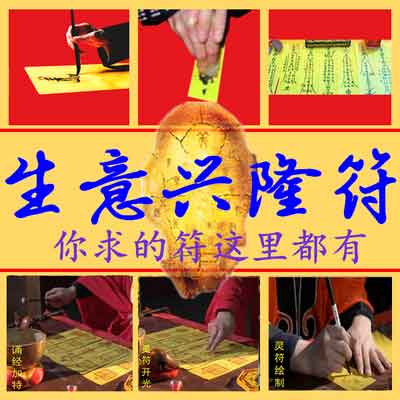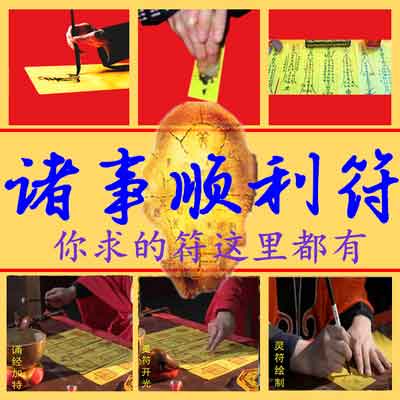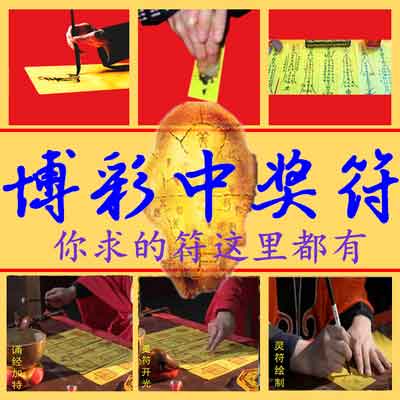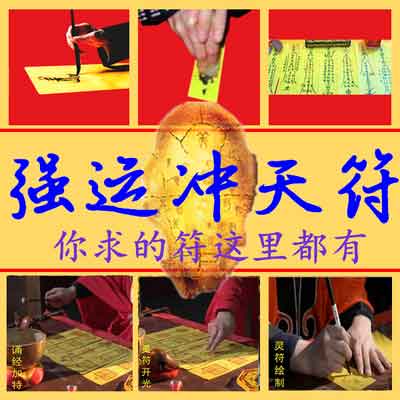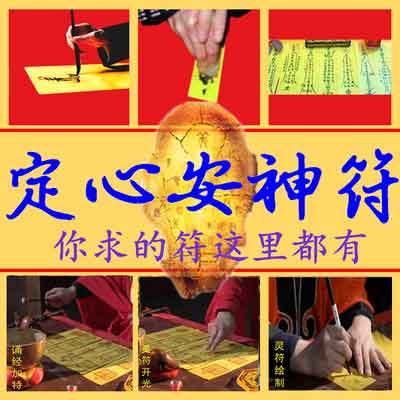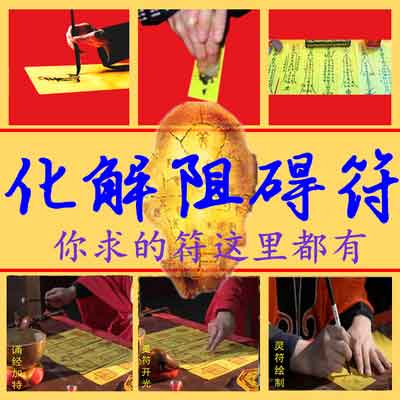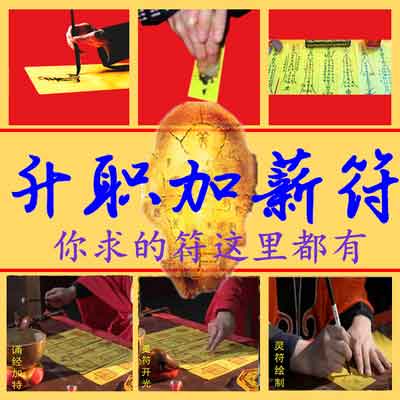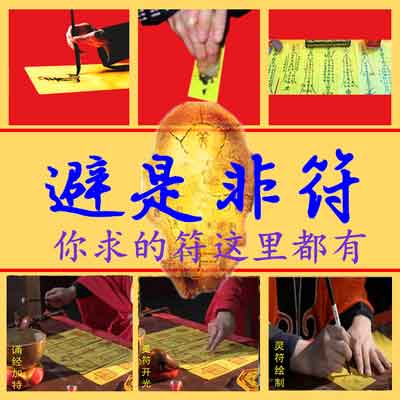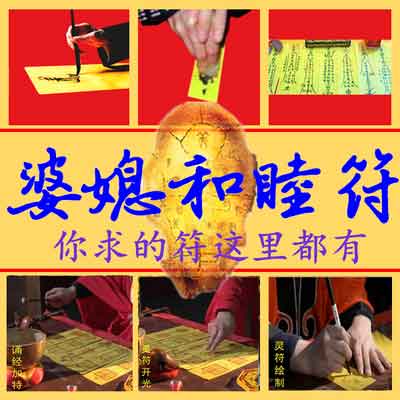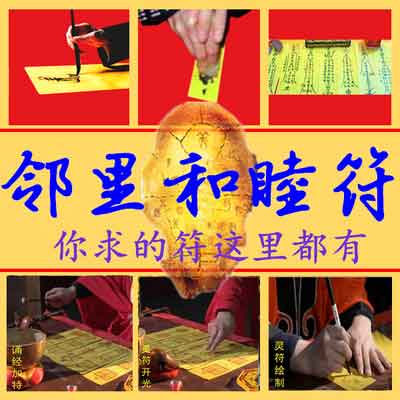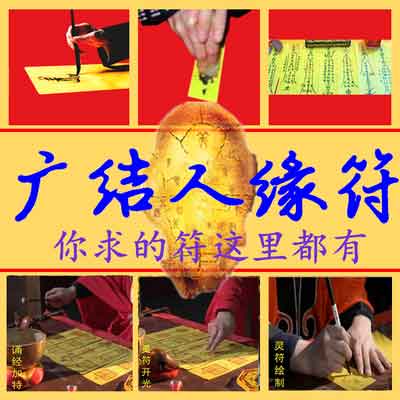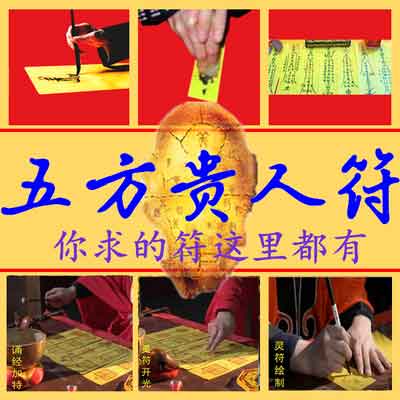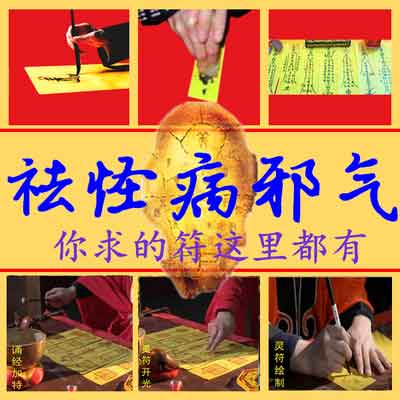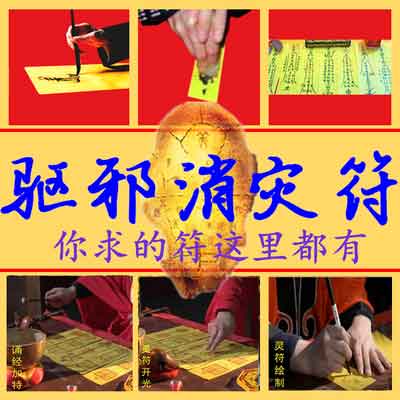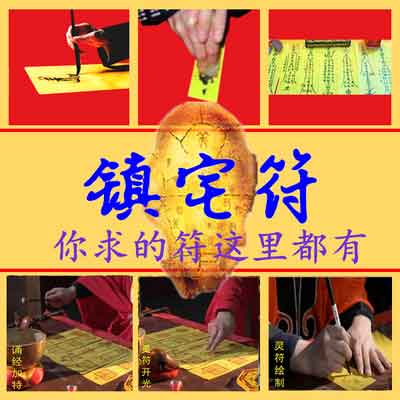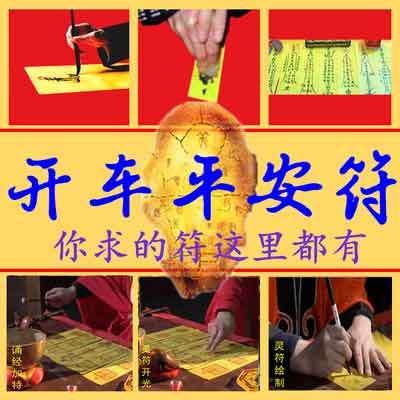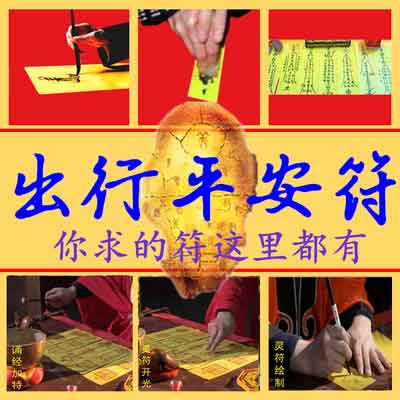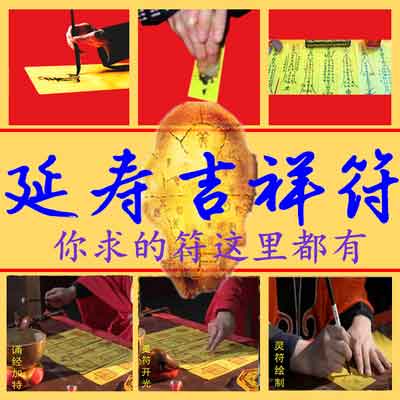论古代文献中的蛊毒及治蛊之术
在我国古代文学和地方文献中,文人墨客以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形形色色的蛊毒。本文尝试把蛊毒加以归类,分为虫蛊、草蛊、药蛊、咒蛊等四类,并归纳出传统治蛊的经验和方法,为研究古代民间蛊毒的种类特点和治蛊之术,以及传统的民间医药、巫术提供资料借鉴。
蛊毒在古代文献、小说中时有出现,我国西南地区民间又把放蛊叫做放歹或放五海。在古代作家笔下,蛊的种类很多,而且各个种类之间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经初步统计,蛊毒大致有以下四类:
一、集百毒于一身的虫蛊
蛊,是一种毒虫。《本草纲虫部四》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食尽诸虫,即此名为蛊”,常见的有毒蜈蚣、毒蜂、毒蝎子、毒蜘蛛、毒蛇等。据说以金蚕为本体的蛊毒对人体危害最大,侵入人的腹中后,会吃光人的肠胃。而且它的抵抗力极强,水淹不死,火烧不亡,就是用力打它也不死。 相传金蚕蛊的表皮是金色的,每天要喂它四分当归,放蛊的方法是把它的粪便放在人的食物中。蛇蛊是在毒月毒日,即每年农历五月五日放养长大的;虱蛊是聚集许多虱虫制成的,若把它摄入腹中,会把人的内脏吃光。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了两则跟虫蛊有关的故事:
其一: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①
其二:鄱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②
“蛊”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为:皿中有虫之象。蛊不论作为疾病名称,还是致病原因,都必然是与虫相关的。《云南风土纪事诗广南府》有载:“‘鱼网高张露坐稀,绿光如火傍檐飞。深夜忽听深凄楚,知是谁家蛊不归。’养蛊者夜辄放蛊害人,故人相戒不敢露坐,张鱼网于檐际则飞高不下,其光如流星而色绿,蛊出不归,则其家呼之,声极哀楚,盖恐为人捕治,则养蛊者必毙。故风雨深夜每闻妇人凄苦之音,余曾欲掩其家而苦无迹,小儿有遭其蛊者,日夜不能眠。亟视其项心有红发一茎,拔之去,饮以□金即吐,滇人有以符水闻治者亦效。”③
又据《滇中琐记飞蛊》载:“石门沈心涯宁守开化,偶晚坐,见空中有流光如帚,似慧星之状,问之胥役,云:‘此名飞蛊,乃蛇蛊也。’畜蛊之家,奉此蛊神能致富,但蛊家妻女,蛇必淫之,蛇必于晚间出游,其光如慧,遇人少处,下食人脑,故开化居民时届黄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④
二、自然界中本性剧毒的草蛊
在云南的原始丛林中,有一种草叫胡蔓草,叶子像莼花,有黄色,有白色,叶子含有剧毒,放入人的口里,人就会百孔出血;叶汁若吞进肚子里,肠胃也会溃烂。当地的莠民常常利用胡蔓草做蛊害人。清人吴大勋,青浦人,乾隆三十七年任云南寻甸知事,三十八年任丽江知府,在其著作《滇南闻见录》中记叙了这样一则故事:
毒草滇南极多。余在顺宁,多有被怨家毒害告官者,案牍累累。案《论衡言毒篇》:草木有巴豆、冶葛,食之杀人。夫毒,太阳之热气也,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故冶在东南,巴在西南。馥谓滇位西南,故多毒草。
除云南有草蛊外,广东省的香山县也曾出现过它的踪迹,当地的莠民也很擅长利用胡蔓草做蛊害人。而且当地的医生也有治胡蔓草剧毒的药方:取母鸡孵过的鸡蛋一个,把它煮熟,研成细末,加一汤匙清油,中胡蔓草毒蛊的人每天服一次,就会吐出胡蔓草蛊。蛊在“上鬲”的,加用胆矾五分,放在热茶里溶化后服用,就会吐出蛊来。蛊在“下鬲”的,用郁金水二钱放在菜汤里服下,蛊也会吐出来。明崇祯时,云南人罗明夔到香山县当县令,了解胡蔓草害人的事情后,就下令:一般人向本县告官的,每人随缴胡蔓草五十枝。令行之下,胡蔓草被大量割除。罗县令亲自监督杂役焚烧收缴的毒草。不久,这种毒草便在香山绝迹。⑤
三、人工合成的药蛊
我国最早详细记载了制蛊之法的是《隋书地理志》:“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厖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如蛇,小者如虱,合置器皿中,令自相食,余一种存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使人食之入腹,蛊食其人五脏。人死则其产业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蛊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在边远的西南地区,僻塞的交通、茂密的原始森林、少数民族的愚昧落后等为蛊毒的发源与滋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用独特的方法制作了其毒无比的药蛊,让世人谈蛊色变。以下两则故事,都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合成蛊毒达到不可告人目的描写:
《滇中琐记沅江蛊》:世传南人能造蛊……独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设宴迎风,花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则合门并命矣!余同寅郡守潘一品,粮厅官素士人父子、主仆、幕宾,皆死此药,无一人得脱者。⑥
又《滇中琐记和合》:滇中无世家,其俗重财而好养女。女众年长,则以归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虑赋谷风,则密以此药投之,能变荡子之耳目,视奇丑之物美如西施,香如苏合,终身不解矣。又有恋药、媚药,饮之者则守其户而不忍去,虽赀本巨万,治装客游,不出二站即废然而还,号曰留人洞。吾乡数十万人,捐坟墓,弃父母妻子老死异域者,大抵皆中此物也。⑦
四、神秘遥控的咒蛊
“蛊”作为古人假想的致命因素,还与鬼神因素纠缠不清,但相比单纯把疾病原因视为鬼神为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病因认识的一种物化趋势。蛊毒远距离作用,也许是奇异的想象,也许是某种疾病的远距离传播,如《滇中琐记放歹》有下面的传说:
迤西南边夷使药害人名曰放歹,药入人腹中,久而成疟不化,人乃渐消瘦,其与人有仇,一念咒语即令人药发而死;其与人有私,一念咒语即令人药发而回头,惟所欲为,无不如意,真可恶也。⑧
这个记录中的“蛊”可以远距离控制被放蛊者,比其他的“蛊”类更为吓人。
另外,《封神演义》中姜子牙、陆牙“发箭射草人”杀死赵公明。《红楼梦》中马道婆剪纸人鬼厌魅贾宝玉和王熙凤,使其差点送了命。《折狱龟鉴》所述梓洲白彦欢假托鬼神作法术诅咒杀人命案等,这些属于咒蛊。
五、古代小说里的治蛊之术
蛊毒确实害人非浅,但它也不是完全无法可救的,古代小说里对治蛊之术也作了不少介绍。根据蛊毒本体的特性,治蛊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其一,治草蛊和药蛊:服用草药土方。
据《太平广记》里关于“治蛊草”的记载:“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⑨
其二,治虫蛊:用枪射击、水煮火烧。
《滇中琐记》里有用枪击飞蛊的故事:“记数年前省城北门,夏月有兵丁夜坐,见有流光六七点,连属而飞如萤,兵知是飞蛊,以鸟枪击之,应手下一虾蟆。然则飞蛊不独是蛇也。炮火纯阳,能制阴邪之物,请即以鸟枪为治蛊之方可也。”⑩
在《滇中琐记蛊毒》中还记录了一种奇特的治蛊之术:“滇中夷妇有养蛊者,小儿多中其蛊,始由脏腑,达于头面,渐渍剥蚀溃烂,不可救药,及其中未久,延蛊医诊之,以水洗患处,盛水铜壶中,紧塞壶口,而引绳悬之屋梁,积薪燃火其下,肆烧煮之,集众围火而坐,烧一时之久,蛊在壶中不胜烧,及鼓荡其壶,向空四击,众不敢近,忽壶塞喷脱,水则跃出,为五色霞光,夺门飞去,水著人头目冷于水雪,竟不温也。烧后儿患稍愈可救,不则难救,蛊被烧时蛊妇在其家自觉烦炙,则出门,径向烧蛊家屋后逡巡招蛊,招之不得,炙极,则跃入湖池中,澡其身而后安,人见之,知为蛊妇,就厮打之,则长跪哀鸣。”⑾
除了医治,我国古代还十分重视对“蛊”的预防。据《周礼》记载,周王室设置了专职官员“庶氏”负责除毒蛊,《周礼秋官庶氏》云:“(庶氏)掌握毒蛊,以攻说桧之,嘉草攻之。”东汉郑玄注:“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对“蛊”这种能病害人的毒物,庶氏采用祭祀祈神(攻说)与药物(嘉草)双管齐下的方法进行祛除。《史记秦本纪》中有国君亲自主持“御蛊”的记载:“(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史记正义》注:“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此注认为“蛊”系致病的热毒恶气,通过以狗祭神来防御蛊毒。
古代小说和文献里的蛊毒种类很多,我国各个地区的蛊毒种类不完全一样,治蛊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治蛊时只有明确了所中蛊毒的种类,有针对性地治蛊,才能达到驱除蛊毒的目的。畜养蛊毒以害人的做法,不但文献中有记载,民间也多有传说,究竟确有其事,还是以讹传讹,至今尚无资料可以证实。然而,即使存在着这种做法,也不能忽视它的可能存在,只有客观科学地面对古代缺乏先进科技文化的深山密林的少数民族奇特的毒蛊传说,面对众多文人笔下让人谈之变色的蛊毒, 并且将它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使我们更深入了解蛊毒传说的源流及其民俗意义。
注释:
⑴ ⑵ 王汝涛主编.太平广记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7:152.
⑶见骆小所主编.西南民族文献第四辑五[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142.
⑷ ⑽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一[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79:133.
⑸见(明)邝露著、蓝鸿恩考释.赤雅考释[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5:36.
⑹ ⑺见丁世良 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卷十一[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1:281.
⑻ ⑾见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卷八十七[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307.
⑼见王汝涛主编.太平广记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7:282-283.
一、集百毒于一身的虫蛊
蛊,是一种毒虫。《本草纲虫部四》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食尽诸虫,即此名为蛊”,常见的有毒蜈蚣、毒蜂、毒蝎子、毒蜘蛛、毒蛇等。据说以金蚕为本体的蛊毒对人体危害最大,侵入人的腹中后,会吃光人的肠胃。而且它的抵抗力极强,水淹不死,火烧不亡,就是用力打它也不死。 相传金蚕蛊的表皮是金色的,每天要喂它四分当归,放蛊的方法是把它的粪便放在人的食物中。蛇蛊是在毒月毒日,即每年农历五月五日放养长大的;虱蛊是聚集许多虱虫制成的,若把它摄入腹中,会把人的内脏吃光。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了两则跟虫蛊有关的故事:
其一: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①
其二:鄱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②
“蛊”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为:皿中有虫之象。蛊不论作为疾病名称,还是致病原因,都必然是与虫相关的。《云南风土纪事诗广南府》有载:“‘鱼网高张露坐稀,绿光如火傍檐飞。深夜忽听深凄楚,知是谁家蛊不归。’养蛊者夜辄放蛊害人,故人相戒不敢露坐,张鱼网于檐际则飞高不下,其光如流星而色绿,蛊出不归,则其家呼之,声极哀楚,盖恐为人捕治,则养蛊者必毙。故风雨深夜每闻妇人凄苦之音,余曾欲掩其家而苦无迹,小儿有遭其蛊者,日夜不能眠。亟视其项心有红发一茎,拔之去,饮以□金即吐,滇人有以符水闻治者亦效。”③
又据《滇中琐记飞蛊》载:“石门沈心涯宁守开化,偶晚坐,见空中有流光如帚,似慧星之状,问之胥役,云:‘此名飞蛊,乃蛇蛊也。’畜蛊之家,奉此蛊神能致富,但蛊家妻女,蛇必淫之,蛇必于晚间出游,其光如慧,遇人少处,下食人脑,故开化居民时届黄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④
二、自然界中本性剧毒的草蛊
在云南的原始丛林中,有一种草叫胡蔓草,叶子像莼花,有黄色,有白色,叶子含有剧毒,放入人的口里,人就会百孔出血;叶汁若吞进肚子里,肠胃也会溃烂。当地的莠民常常利用胡蔓草做蛊害人。清人吴大勋,青浦人,乾隆三十七年任云南寻甸知事,三十八年任丽江知府,在其著作《滇南闻见录》中记叙了这样一则故事:
毒草滇南极多。余在顺宁,多有被怨家毒害告官者,案牍累累。案《论衡言毒篇》:草木有巴豆、冶葛,食之杀人。夫毒,太阳之热气也,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故冶在东南,巴在西南。馥谓滇位西南,故多毒草。
除云南有草蛊外,广东省的香山县也曾出现过它的踪迹,当地的莠民也很擅长利用胡蔓草做蛊害人。而且当地的医生也有治胡蔓草剧毒的药方:取母鸡孵过的鸡蛋一个,把它煮熟,研成细末,加一汤匙清油,中胡蔓草毒蛊的人每天服一次,就会吐出胡蔓草蛊。蛊在“上鬲”的,加用胆矾五分,放在热茶里溶化后服用,就会吐出蛊来。蛊在“下鬲”的,用郁金水二钱放在菜汤里服下,蛊也会吐出来。明崇祯时,云南人罗明夔到香山县当县令,了解胡蔓草害人的事情后,就下令:一般人向本县告官的,每人随缴胡蔓草五十枝。令行之下,胡蔓草被大量割除。罗县令亲自监督杂役焚烧收缴的毒草。不久,这种毒草便在香山绝迹。⑤
三、人工合成的药蛊
我国最早详细记载了制蛊之法的是《隋书地理志》:“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厖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如蛇,小者如虱,合置器皿中,令自相食,余一种存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使人食之入腹,蛊食其人五脏。人死则其产业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蛊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在边远的西南地区,僻塞的交通、茂密的原始森林、少数民族的愚昧落后等为蛊毒的发源与滋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用独特的方法制作了其毒无比的药蛊,让世人谈蛊色变。以下两则故事,都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合成蛊毒达到不可告人目的描写:
《滇中琐记沅江蛊》:世传南人能造蛊……独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设宴迎风,花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则合门并命矣!余同寅郡守潘一品,粮厅官素士人父子、主仆、幕宾,皆死此药,无一人得脱者。⑥
又《滇中琐记和合》:滇中无世家,其俗重财而好养女。女众年长,则以归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虑赋谷风,则密以此药投之,能变荡子之耳目,视奇丑之物美如西施,香如苏合,终身不解矣。又有恋药、媚药,饮之者则守其户而不忍去,虽赀本巨万,治装客游,不出二站即废然而还,号曰留人洞。吾乡数十万人,捐坟墓,弃父母妻子老死异域者,大抵皆中此物也。⑦
四、神秘遥控的咒蛊
“蛊”作为古人假想的致命因素,还与鬼神因素纠缠不清,但相比单纯把疾病原因视为鬼神为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病因认识的一种物化趋势。蛊毒远距离作用,也许是奇异的想象,也许是某种疾病的远距离传播,如《滇中琐记放歹》有下面的传说:
迤西南边夷使药害人名曰放歹,药入人腹中,久而成疟不化,人乃渐消瘦,其与人有仇,一念咒语即令人药发而死;其与人有私,一念咒语即令人药发而回头,惟所欲为,无不如意,真可恶也。⑧
这个记录中的“蛊”可以远距离控制被放蛊者,比其他的“蛊”类更为吓人。
另外,《封神演义》中姜子牙、陆牙“发箭射草人”杀死赵公明。《红楼梦》中马道婆剪纸人鬼厌魅贾宝玉和王熙凤,使其差点送了命。《折狱龟鉴》所述梓洲白彦欢假托鬼神作法术诅咒杀人命案等,这些属于咒蛊。
五、古代小说里的治蛊之术
蛊毒确实害人非浅,但它也不是完全无法可救的,古代小说里对治蛊之术也作了不少介绍。根据蛊毒本体的特性,治蛊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其一,治草蛊和药蛊:服用草药土方。
据《太平广记》里关于“治蛊草”的记载:“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⑨
其二,治虫蛊:用枪射击、水煮火烧。
《滇中琐记》里有用枪击飞蛊的故事:“记数年前省城北门,夏月有兵丁夜坐,见有流光六七点,连属而飞如萤,兵知是飞蛊,以鸟枪击之,应手下一虾蟆。然则飞蛊不独是蛇也。炮火纯阳,能制阴邪之物,请即以鸟枪为治蛊之方可也。”⑩
在《滇中琐记蛊毒》中还记录了一种奇特的治蛊之术:“滇中夷妇有养蛊者,小儿多中其蛊,始由脏腑,达于头面,渐渍剥蚀溃烂,不可救药,及其中未久,延蛊医诊之,以水洗患处,盛水铜壶中,紧塞壶口,而引绳悬之屋梁,积薪燃火其下,肆烧煮之,集众围火而坐,烧一时之久,蛊在壶中不胜烧,及鼓荡其壶,向空四击,众不敢近,忽壶塞喷脱,水则跃出,为五色霞光,夺门飞去,水著人头目冷于水雪,竟不温也。烧后儿患稍愈可救,不则难救,蛊被烧时蛊妇在其家自觉烦炙,则出门,径向烧蛊家屋后逡巡招蛊,招之不得,炙极,则跃入湖池中,澡其身而后安,人见之,知为蛊妇,就厮打之,则长跪哀鸣。”⑾
除了医治,我国古代还十分重视对“蛊”的预防。据《周礼》记载,周王室设置了专职官员“庶氏”负责除毒蛊,《周礼秋官庶氏》云:“(庶氏)掌握毒蛊,以攻说桧之,嘉草攻之。”东汉郑玄注:“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对“蛊”这种能病害人的毒物,庶氏采用祭祀祈神(攻说)与药物(嘉草)双管齐下的方法进行祛除。《史记秦本纪》中有国君亲自主持“御蛊”的记载:“(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史记正义》注:“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此注认为“蛊”系致病的热毒恶气,通过以狗祭神来防御蛊毒。
古代小说和文献里的蛊毒种类很多,我国各个地区的蛊毒种类不完全一样,治蛊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治蛊时只有明确了所中蛊毒的种类,有针对性地治蛊,才能达到驱除蛊毒的目的。畜养蛊毒以害人的做法,不但文献中有记载,民间也多有传说,究竟确有其事,还是以讹传讹,至今尚无资料可以证实。然而,即使存在着这种做法,也不能忽视它的可能存在,只有客观科学地面对古代缺乏先进科技文化的深山密林的少数民族奇特的毒蛊传说,面对众多文人笔下让人谈之变色的蛊毒, 并且将它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使我们更深入了解蛊毒传说的源流及其民俗意义。
注释:
⑴ ⑵ 王汝涛主编.太平广记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7:152.
⑶见骆小所主编.西南民族文献第四辑五[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142.
⑷ ⑽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一[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79:133.
⑸见(明)邝露著、蓝鸿恩考释.赤雅考释[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5:36.
⑹ ⑺见丁世良 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卷十一[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1:281.
⑻ ⑾见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卷八十七[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307.
⑼见王汝涛主编.太平广记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7:282-283.